
口述 《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》主校 釋如密
整理 張殿文
問一、您是最早思考推動翻譯工作組織化的學僧,誠如主譯如法師提及,老師成立譯場之後,他常與您討論譯場的運作,可否談一談這譯場工作如何規劃和進行?
答:從鳩摩羅什大師在漢地開始翻譯經典,規劃整個譯場各種功能和運作形式;唐朝玄奘大師主持的譯場,則在 19 年間就翻譯出一千多卷的經典,這都是譯場的輝煌時代,可做為我們借鑒學習和吸收的對象,讓我們譯場能夠盡量採納歷史上最佳、最完備的作法。
鳩摩羅什大師的譯場運作,主要以上午譯經,下午就以講論為主,所有的人都能夠接收到大師的講論,而玄奘大師應該也曾借鑒鳩摩羅什大師開設譯場的角度,所以玄奘大師進一步知道必須集結菁英人力來翻譯,而不是以數量眾多的人力取勝,才能達到學識傳遞的效果。
為什麼不過 20 年左右的時間,玄奘大師卻能夠翻譯一千多卷經典?玄奘大師所主持的譯場,很值得我們去深入了解。玄奘大師譯場有一特色,他的人數不算很多,但是必須是全國裡面的菁英人才,從當時各省各府之中,從各主要大城市中,只挑選其中一、兩位出家人出來擔任譯經院裡主要職務。
這些職務包括幫忙傳遞、記錄玄奘大師翻譯文字的各種工作,也有對於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文字上、義理上提出質疑、甚至不同意見的工作,而翻譯和講論經典也同時進行,當時是以一時之選來參與最核心的譯場工作。
特別是玄奘大師在印度留學非常長的時間,又久駐「那爛陀寺」研修,了解當時印度各地不同部派的說法,所以譯經院會進行很詳細的紀錄,甚至當時記錄譯師們有疑問時,會直接去問玄奘大師來進行校對。
這些來自各省各府的一時之選,他們學完譯完這些經論之後,回到自己所來當地講學,由於本是當地重要的菁英大德,所以也能夠直接將玄奘大師所翻譯經論的這些內涵,帶回各地,這也是玄奘大師從全國當地挑選菁英僧才的第二個目的,主要是為了未來繼續講述經典的內涵,由這些菁英僧才直接傳遞到當時全國各地。
我們則是借鑒了玄奘大師挑選擅長各領域最重要的僧才,採納各專業的部分,每一方面工作我們都要確實要找到最主要擅長的法師來負責工作,比如像如吉法師從年輕時,一直在行文潤色方面深具造詣,我們就會請他負責「主潤」部分,對於很多古文白話翻譯方面的文飾,大家若有不同看法,就會請他做為潤色方面的最終裁定。

我們為什麼會設置「眾校」、「眾潤」,也是源於玄奘大師的譯場。中國歷史上譯場發展的方向,一直到宋代譯經院模式,也是延用唐朝方式,像北宋初年的譯經院構造為三堂,中為譯經,「西序」為「證義」,跟玄奘第一類助手的名稱完全相同;「東序」為「潤文」,也跟玄奘第二類助手的「綴文」同樣關乎文筆工作,實際上就是一邊負責義理上面的提問,一邊是負責文字上面的潤色,當「義理」上面覺得可以過,但是「文字」上面不能過的時候,「文字」那一方的法師就會退回這個譯文,希望能夠重提出文字的修改。
而中間主譯部門,也負責主理配對,像我們現今行政組的法師一樣,負責傳遞文本,把負責潤色法師所提出來的意見,以及修改過的這個文稿,再重新交給「西序」負責校對的法師,考慮這麼改可不可以,那校對群組的法師,會再次檢視修改的文稿,如果這個文字是到位的,就可能採納,或者他會覺得說,這樣子改了以後,原意就被扭曲了,或者產生一點偏差,他就可能會不同意,加以否決,或者重新提出另外一種翻譯方式。
以我們現今譯經院流程來看,一開始主譯如法法師會進行《四家合註》原文翻譯成漢文的流程,接下來他這個文本,會交給「考據」的譯師、「審義」的譯師、「校勘」的譯師、「語譯」的譯師,請他們在這一個文本當中完成所要負責的部分。
這時候開始就會針對主譯法師所翻譯的文本的每一段落,要考證的進行考證,對於法相要解釋的進行解釋,版本若有異同要進行校勘,古文開始進行白話翻譯,這時候產生了第一次完整分工。分工完畢之後,行政組法師將這些各組譯師所負責的內容全部收集起來,並且配上原來的主譯譯師的原文合成為一個版本,這個版本會交到主校的手上,也就是我的手上。
誠如上述,我們譯經院「眾校」、「眾潤」的設置,是參考過去譯場中分成「東序」、「西序」負責校對和潤文的方式,發展出「眾校」、「眾潤」這兩個職能,後來這部分一直是歷史上譯場的主要架構。北宋是歷史上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組織譯場,北宋到南宋,是比較動盪的時代,一直到元、明、清,因為印度方面佛教已經滅亡了,所以後來再也沒有印度的高僧來到中國,中國的譯經事業算是暫時的中止,一直要等到下一次的譯場開設,也就是法尊法師開始才再有譯場的組織。
法尊法師的時代雖然譯場重開,但是主要只有兩種人員:一是翻譯的譯師、另一就是能夠解答疑難的高僧,而當時擔任解答疑難的就是他的一位老師──東本仁波切。法尊法師請他到漢地來參與譯經工作,擔任解答疑難的角色,將漢文《大毗婆沙論》重新翻譯成藏文,回饋給藏地。
所以從歷史上得知,祖師大德同樣在翻譯過程當中,會遇到和我們一樣所不能理解的疑問,當我們自己不能裁決的時候,最好的就是能夠請教師長,因此,參考藏系的譯經院體制,在我們所有組織當中,最頂尖或最高的詢問者,就是我們所設立的「授義」這一個職稱,也就是他能夠「傳授」這個經論翻譯裡中,一段話乃至一個字詞真正的「義理」為何。
至此我們的譯經院的架構,實已結合了漢、藏兩地的千年傳統,當我們譯師們集體討論之後,也無法達成一致共識或者無法解決這疑惑時,我們就會請教師長授義,幫我們解答這些疑惑。

問二、譯校整本《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》內容之前,譯經院如何決定全書的體例和欄目,每一種欄目安排的思考理路為何,如何達到傳承目的?
答:《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》的書名放進「校註」二字,說明本書不僅單純將《四家合註》原文翻譯出來而已。當初真如老師召開譯經會議,就提醒大家首要考慮讀者大眾的感受,希望譯文能夠非常地流暢,乃至於像是詩歌般優美,讓讀者賞心悅目、產生恭敬心,油然生信,進而學習深入。
這也是本書欄目安排的考量,能夠饒益到廣大的眾生。首先是「原文」部分,從「藏文」譯成「漢文古文」,傳譯古人的文字,做完整流暢的譯寫,這是「原文」部分所做安排。
同時,要照顧到廣大居士學習時閱讀古文會有困難,所以我們再將古文翻譯成白話,這也是「語譯」部分,白話文讓大眾更容易開始入手閱讀。而且我們不用「漢文古文」翻譯成「漢文白話」,而是直接用「藏文」翻譯成「漢文白話」,讓「語譯」更加貼近原文,從「原文」到「語譯」的過程中,譯師彼此之間用字遣詞風格不同,都可能會造成閱讀上障礙,所以又進行一次潤稿的統合。
再者,許多廣論同學在學習中,可能對於法相內涵、時空由來,甚至是祖師行誼甚不清楚,所以《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》也希望透過學習五大論的法師所了解的經論依據,將學習上的不清楚的部分,經由註釋說明清楚,因此書中安排了「註釋」跟「說明」兩個欄目。
進入「註釋」這一個欄目,為了提升經典翻譯的精準性,了解歷代經論對於這些法相是怎麼詮釋的,乃至於說宗大師在《廣論》裡,或者《四家合註》提到的經論,我們都盡所能找出起源,把相關經論的依據,全部都尋找出來,如果有中文譯本的出處,我們甚至提供古德的翻譯。用詞用字都有依據,讓讀者大眾能夠了解最正確、最真實的法義。比如論典是引用《大藏經》其中一部經論,除了漢文的頁數,甚至是藏文的《大藏經》,我們也提供了頁數。
另外,祖師的生平、地名,都由負責考據的譯師來負責,而關於法相的部分,比如像是「菩提」、「次第」是什麼意思,乃至於我們之前學過的「文殊」、佛的「語功德」當中所提到的「六十四韻音」到底是哪六十四種,從法相的專業尋找、考察,則是由「審義」譯師負責義理上的定奪。
「註譯」當中還有「訓詁」譯師負責漢文古文的詞義解釋,因為多數現代讀者對於古文的用詞不是很熟悉,為了避免誤讀,需要進行字面上的解釋。這部分我們是禮請對訓詁素有專業的蔡纓勳老師負責。
緊接著我們再另闢一個欄目「說明」,有些祖師會對一個問題產生不同理解,大眾學員應該如何去了解,於是就進行一個說明,其次「說明」也針對於一些可能會產生懷疑的重要義理,進行一些分析,這部分也是「審義」譯師來負責的。
最後,為了儘量的還原《四家合註》最原本面貌、或者是詮釋這一本經論最精準的原文表達,所以我們還安排「校勘」的進行,這是第五個欄目。
而「校勘」的工作,就是將許多版本收集起來,並且進行比對,提供《四家合註》最有可能還原的版本,負責這項工作就是「參異」的譯師負責。經論流傳下來不同版本,產生一些不同的內容,一字之差都有可能導致誤解,我們想辦法儘可能地把不同版本都收集起來,並且經過一番的比對,然後再去判斷。
從這五個欄目決定之後,衍生需要完成這幾項工作的譯師們,我們希望能夠集眾人之力,組織一個有系統的方式、配合大家的專長,貫徹真如老師所提示的原則,這是一個譯經院的基本信念。
問三、譯場的分工如此複雜,您又是如何掌握進度和流程,在今年順利推出《四家合註》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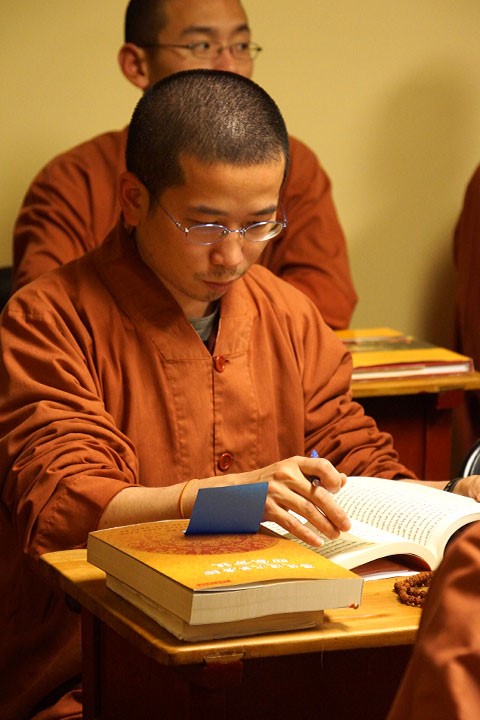 答:主校工作一大部分,在維持譯場的秩序,按著流程能夠順暢地完成既定目標。所以我對於流程必須比所有人熟悉。誠如上述,我收下第一次分工後的文本,開始進行第一次校對,主要針對譯文所註解等所有內容,先全部讀過一遍,讀完後提出我認為可能要修改、或者我覺得還沒有註釋到、有疑問的部分,我提出註釋和疑問的版本,也成為「初校版」的基礎。
答:主校工作一大部分,在維持譯場的秩序,按著流程能夠順暢地完成既定目標。所以我對於流程必須比所有人熟悉。誠如上述,我收下第一次分工後的文本,開始進行第一次校對,主要針對譯文所註解等所有內容,先全部讀過一遍,讀完後提出我認為可能要修改、或者我覺得還沒有註釋到、有疑問的部分,我提出註釋和疑問的版本,也成為「初校版」的基礎。
行政組的法師會將我所提出來的所有意見,修改成一個版本,稱之為「初校本」,複印出來就發下去給「眾校」和「眾潤」進行不同工作。而「眾校」和「眾潤」部分,分成了十幾位法師跟幾位國文老師,因此可能會形成十幾個版本。那時候我們的要求是希望五天要完成一個段落,所以這些「眾校」、「眾潤」,五天內不但要完成,還包括了行政組的法師要把所提出來的意見收集起來,發給下一階段譯師進行處理。
這十幾個版本收集起來以後,會交給合校潤的譯師,他也是要在五天當中,將十幾個版本篩選出真的要讓主譯、主校、主潤、審義譯師等參考的內容合成一個新的版本,這個版本就會稱之為「二校本」。
二校版本形成之後,往下就交給了「提疑」,包含部分的法師,及大部分居士負責,我們當時也是儘量要求在五天當中要完成這提問程序。
所以像陳學長可能忙於園區不可開交時,還是要抽出一段時間將「二校本」在五天之內閱讀完,提出他的意見。
「提疑」完畢之後,我們會進行統整,因為提疑、提問的法師跟居士也是十幾位,所以要把重複的及不重複的收集在一起加以分類,分類成「義理上」及「文字上」的部分,由我負責綜合成一本,接下來進行「釋疑」這部分就由三主譯師,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主譯、主校、主潤為主,還包括了審義法師,因為他是審定義理的譯師,主要由這四位法師負責。
我們幾位集合在一起討論,對於法師、居士所提出來的疑問,我們反省一下,是否真的有考量到他們的立場,這樣子翻譯出來讀起來順不順,或者說他們可能單純從中文上面來看可能會理解錯誤,也就代表這個文字可能要進行修正。
「釋疑」也是 2014 年年底最重要的工作,我們那時候密集的程度,一天可能要花三、四個小時,針對法師、居士所提出來的問題彼此進行討論,然後去裁決說要不要改。
到了 2015 年,當「釋疑」完成,主譯又將所有的文字都讀過幾遍,進行一次調整,等於是「三校本」就出來了。我們就將「三校本」交給南海寺法師去進行核定,並且製作科判。她們在閱讀過程當中,也提出了一些意見,同時我們也考慮了很多的內容可能還需要更多人去參與。
所以 2015 年整年度,譯經院的各譯師一起進行了「大會校」,意思就是針對「三校本」及南海寺法師提供的意見,以各組的專業重新去審查一遍;內容是否正確、體例是否有誤差,甚至標點符號對不對,然後三主譯師要對於所有的文本整個通讀一遍,如果在譯場討論過程當中,由於觀點歧異太大,討論欲罷不能,就會把這個問題儲存起來,交給主譯法師做最後的仲裁。
整個大會校進行了快一年,一方面是累積經驗,一方面老師要我們一再地檢驗斟酌,希望審慎行事,所以整個《四家合註》又用將近一年的時間,進行詳細校對,一直到 2015 年 11 月才初步把第四次的校對完成。
雖說是「第四次」校對,這是就集體合作校對而言的,其實如果包括個人通讀校對,以及請南海寺法師她們進行過三、四遍校對,加上行政組法師及請出版專業團隊所進行的十餘次校對,這樣子的反覆校對就已超過十幾遍。去年 2015 年年底時,主譯法師就曾提到,他自己進行的校對也可能就超過了三次,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一冊《四家合註校註集》,整本可能已經過將近二十遍的這個校對,也印證了眾人和合之力,才能完成師長大德的志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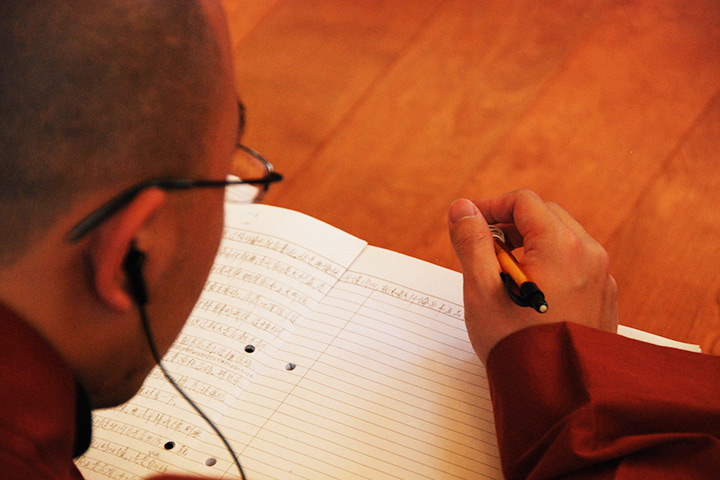
問四、自古以來譯場也是講經場、辯經場,譯經成為求真求理求道的過程,在譯經和譯經院建立過程中,真如老師如何啟發譯師的工作?
答:譯經是真如老師特別重視的事業。我們甚至聽過真如老師如此描述:假設當要她把所有事業全部放下,有一個事業她不會放掉,畢生乃至生生世世都不會放掉的,就是譯經這個事業,她永遠會一直參與下去。
這對我們是非常大的加持,從譯經院所翻譯的第一本經論《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》開始,真如老師就隨時會聽取彙報,隨時了解我們翻譯的進度,關照著譯經院發展,哪怕對於這本校註集要怎麼設計,封面、顏色、甚至字裡行間顏色的配對怎樣較好?設計上可能是一個花紋、圖形、或者是精裝、平裝、用什麼材質、紙質,非常繁瑣或者微小的工作,真如老師都是十分重視每一個細節,都會親自的去參與。
這代表真如老師對於譯經院的期許,希望我們透過翻譯的當下,就是在學習,翻譯的當下,就能夠提升內心,包括了我們「身」、「語」、「意」三業上都能夠達到提升。
從「身」角度來講,我們每天進行各種翻譯工作時,真如老師會不時現身,了解我們當時進行得如何,而威儀是否保持讓人能夠生信的態度,或是我們彼此討論時的談吐,是否保持一個恭敬「三寶」的心態。為什麼老師會如此重視這些細節呢?因為這經論本身要傳達的「業力」,會在譯師們的「三業」當中傳遞出去,所以我們在面對經論時,就應該要有虔誠恭敬的心態。
從「語」方面來講,譯師們討論經典時,乃至對話的音量是否對於經論時時飽含著敬意,真如老師都會從我們討論過程中聽得出來;提策我們翻譯經典,不是只用文字翻出來就好,而是在身、語這個當下,就能夠因為翻譯經論而獲益。我們也因此更能夠體會到彼此之間都相當的重要、缺一不可。所以我們譯經的討論,不會成為意氣爭論,而是成為我們更深刻了解對方的一個助緣,這是在身、語的方面的學習。
在「意」的部分,除了前面提到翻譯經論必須達到非常精準,且這種「精準」是遠遠超越我們所能認知的標準。
一般我們覺得「精準」,可能就是用藏語中某個詞,配對到中文時等同於某個詞,如果沒有錯,覺得就夠了。但老師的認知並不是僅此而已,所謂「精準」,包含這一個詞彙用出來時,讀者們會不會因此產生反省,產生對自己「業力」的省察,或者說翻譯者對「業力」的省察,透過譯文,讀者在讀的時候會不會產生恭敬的心態,進而提升意樂。
譬如在原文當中,我們翻譯「作業」一詞之時,會覺得在現代用語「作業」就像是回家做功課這種感覺,所以就會想要改成「作用」一詞,一種產生效能的意味,較符合現代感。但是真如老師就會提醒我們,有沒有想過經論中為什麼要用「作業」一詞呢?當人們看到這個「業」字時,當下就要反省現在所造的「業」,或者說我們現在的心態是否是符順「業果」見解,這個心態是否向善?
真如老師的教導,做為主校的我有很大啟發,「作業」一詞感覺很稀鬆平常,但是要達到祖師們的精準度,在我們的認知裡必須還要再提升:看到這個文字的當下,還要想到文字對自己生命無限的影響性。
真如老師希望透過這些文字,也能夠讓眾生能夠產生對於三寶的崇仰、對於上師的念恩。比如之前學習到「六十四韻音」階段,一開始我們的註釋很簡單,就是文殊菩薩或者佛的「語功德」之一,從六十四種角度闡述語方面的功德。但是真如老師就希望書中能註明這「六十四韻音」到底是哪六十四種?所以審義法師開始考察出來不同的說法,並一一羅列,如果再將六十四種不同說法都並列時,至少就是一百二十八種了!把各相全部並列以後,我們覺得這樣應該就夠了,但是真如老師又進一步的提策,每一種解釋,看起來就只是一個詞彙,但是這些詞彙到底表達什麼內涵呢?讀者可能還是不知道,所以譯師需要去考察出每一韻音的功德是什麼意思。(請參見《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》第一冊第 69 頁)
如果只是從一般「註釋」角度來看,譯師的心態會覺得越簡單越好,讀者知道是一個語功德就好了,詳細羅列這麼多,估計讀者也不會想看,可能就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,覺得這樣解釋就好了,而且也沒有錯。
可是真如老師提策的重點是,當大家真能了解六十四韻音的內涵,就會知道佛的說法功德、文殊菩薩的語功德原來如此,透過知曉「語功德」內涵,就是在對佛菩薩修隨喜、修崇仰的信心。
註釋當下,本身就是學習皈依的學處,就是在修行,其實很不簡單。這部分如果沒有真如老師教導,雖然我們會儘可能做到翻譯精準,但是真如老師心目中的期望,仍比我們想像中高出非常多的。
因此,我們非常願意繼續投入譯經工作,正是因為真如老師能夠帶領我們深刻體會當下如《廣論》所說「將一切聖言現為教授」、「當下聞思即是修行」。
如果沒有老師引領這個譯經院的教導,其實我們很難真正去體會到「金字塔」頂端到底是如何崇高,因此所有加入譯經院的同學們,從來都沒有生起過想要退出的想法,這樣子的跟隨真如老師學習翻譯實在是太美了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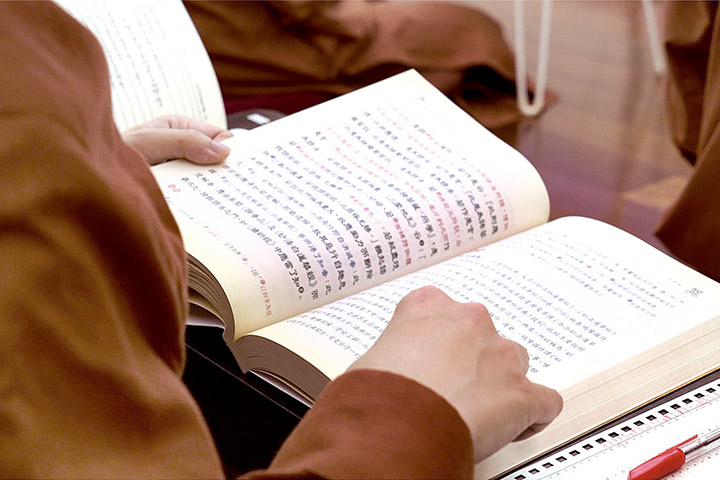
文章來源:《福智之聲》227期

心得回饋
為維持良好的線上環境,留言需經審核方會呈現,請見諒。